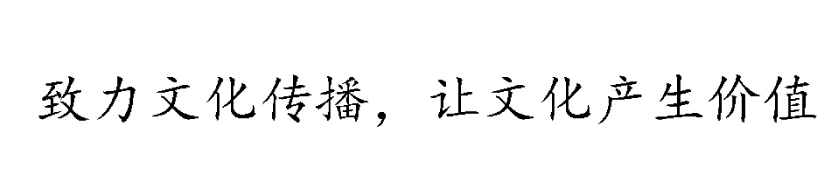中尚图动态
爱好文学曾经军人发掘生活出书短篇小说集
时间:2021-10-18 14:40:42 来源:中尚图

你从未离开
迎风飞舞的身体
像撒在黑夜中的种子
我要和你一起生长
奔向黎明


1--.
薇想把这种感觉说给父亲听,可他不在了。


也许,父亲并不想知道这些。
谁知道呢?
·抚慰·


最近,每天这个时刻,薇都陪父亲出来散步。天慢慢黑下来的时候,但也不能太黑,沿着107国道一直走到科大,这比原来的距离缩短了三倍可能都不止,可耗用的时间基本和以前一样。父女间虽没多少交流,但总会发现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有趣事物,路边新建的房子、新栽的树以及其他的每日都会出现的变化。还有天气,每天都更热一些,日甚一日的热火朝天的变化。
薇和父亲住在干休所,但这里不属于他们,是爷爷奶奶才有资格住的地方。院子里新建了两栋灰色的大楼,不过,仍然保留了许多挺占地方的老式平房。那些陈旧的老房子并不奢华,可薇觉得,就是这种陈旧感才留住了以前的荣耀和优越感。往里走,完全脱离了外面的喧嚣,甚至于经过的汽车都会小心地放慢速度,没有人大声喧哗或弄出什么声响,几个老式的路灯有气无力地照在路面上,像银色的沙子。再往前走,拐个弯,就是他们的房子。
从外面看,只有一个房间的灯亮着。的确是这样,薇的奶奶去世后,这套大房子里就只有他们父女了。更早一点的时候,大部分时间,只有薇的父亲一个人住。
电影没看成。快开映的时候,薇想到了父亲。她记得,本来要帮他换内衣的,还要准备他该吃的药,以及再买一大瓶止血剂。
此刻,薇在门前跺着脚,用马尾做的像拂尘一样的东西抽打着裤脚。这不是多此一举,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清除灰尘,另外,也是住在这里多年养成的习惯。爷爷他们一直都是这样,进门前要打掉灰尘,但奇怪的是,他们进屋从来不换拖鞋,即使是回到自己的卧室里。薇想过这件事,也许老人家觉得穿拖鞋会增加某种不确定的危险。而薇保持这样做的理由,很难说不是一种敬畏,她享受只有回到这里才有的特殊仪式。
当她还在外面的时候,父亲已经不行了。


事实上,他一直不舒服。床旁边的桌子上放着各种药,胡乱地堆放在老式的录音机前面。止痛药吃完了,还没来得及开新的,其中有几盒是治抑郁症的,还有所剩不多的止血剂。后来,当薇收起这些药准备扔掉的时候,她想象了当时的情景,父亲肯定想说些什么,想说什么呢?是怨恨最后的时刻,自己不在眼前,或者是自己出去的那一刻,他已经快失去意识了,还是他一直就这样躺着,一动不动地看着白色的天花板,盼望那一刻降临?
父亲喝水的杯子已经空了,水没洒出来,这让薇觉得有点意外。因为没来得及换下尿不湿,此刻,父亲的身子下面有明显的水渍。那一刻,他一定很不舒服,可这情况并不算严重,他宁愿这样,也比死了强得多。枕头旁还有一些摊开的书和一本日记,看来,他并没有料到死神在那一刻会突然降临。
天气不合时宜的温暖和晴朗,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客厅地板上。薇开始想象,父亲死前经历的痛苦,或是没来得及痛苦就已失去了生命。她和父亲曾经讨论过他的病情,有些话,薇说得不明确,但父亲却不会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变化。他们俩心照不宣,像等着一件将来必然发生的事慢慢逼近。薇设想自己一定会在场的,说不定会像小说或电视剧中描述的那样,既痛苦又神圣,放着他喜欢的音乐,枕头和其他物品已摆放好,她穿戴整齐,然后拉来一把椅子。这样,她就可以拉着他的手,看他断断续续地诉说自己最后的心愿或披露一些重大的隐私。她父亲会喜欢那种仪式的,只是不喜欢拉着手。最近散步的时候,他对她用力握着的手很不习惯,总试图挣扎和摆脱,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徒劳无益,他已经无法仅仅靠自己的力气步行那么远了。
“你不要这样用力拉着我。”
“你有可能站不住。”薇对父亲突然的不满有些不解。
“放手吧,我又不是残废。”
“嗯,你不是残废?你不是吗?”薇在心里大声咆哮着。
他想的大概是如何维护一个父亲的尊严,病人的尊严。而后者更容易被人羞辱和瞧不起,他不想这样,但又无可奈何。
尽管如此,薇还是感觉突然,太突然了。虽然医生让她有心理准备,可她忙得没顾上准备那些死人要用的东西。墓地是她和三民叔叔一起去买的,父亲将和他的父亲埋葬在一起,在同一座山上,是一座离此不远的秀丽的山。这也算一种团聚,不是吗?
薇不清楚父亲到底有没有留下什么信息。起码,应该有一份遗嘱,尽管他的财产差不多都是从爷爷那里获得的,不太多,但他应该这样做吧。大多数时间里,他习惯用笔记录下自己的计划。可这次,父亲以这样快又这么不近人情的方式离开,还是让薇感到了困惑和悲伤。薇和父亲曾谈论过,忍受无助、痛苦和自我反感的极限,意识到那个极限的可能性和重要性,而不是省略过去或别的什么。


宁可早点,不是晚点。
人生就像行在山路,在某一时刻,被一股有些粗鲁的山风吹醒,忽然发觉风景在不断倒退,同行人或走或停,而自己始终向前,不可改变,无法转身。
2.
也许应该先坐着他的车,随便去什么地方。
比如,阿拉善,她愿意去感受一下
那种清凉又令人窒息的无人区。


·三十二立·
店里的装修风格明显偏男性化。有两个女人在聊天,声音不高,但张扬的东北话毫不收敛,大概聊得不开心,没有在陌生人或朋友面前应有的礼貌。经过时,健雅瞟了她们一眼,觉得像是两姐妹,虽然其中一个的脸更娇嫩,额头也更宽阔。她们肯定是一起来的,不过坐得不亲密,或许正因为什么事情闹得不愉快。
“你愿意坐在哪里?”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叔问,“坐沙发?那儿靠着窗也舒服一些。”然后,他推开柜台的侧门,迎面走来。
健雅注意到了他的手,像做医生的姑夫一样,纤细而苍白。
“有什么要点的吗?很抱歉,这个时候不能全都供应,不过还是有六七种可以选择。”他把菜单递给健雅,“有两款点心是我今天试着做的,味道还可以。不过咖啡要现磨,可能得多等几分钟。”
“那就试试今天的运气。”健雅点了他推荐的咖啡,又对着窗户里的自己说,“就当下午茶了。”
健雅这次没看手机,而是把刚才看的书摊到桌上。没有人在对面,身后的位子也没有人,空旷带来了安全感。此时,她忽然觉得请假看书比看电影更不靠谱,又很快在心里安慰自己,这毕竟是生日的一部分。
健雅拿起咖啡,喝了一口,味道很浓,不过正合她的口味。她决定喝完这杯后再要一杯同样的。偶遇一杯合心意的咖啡,也是需要缘分的。其实,她一直觉得咖啡比烈性酒更能让她感到兴奋和安慰。
两个女人懒洋洋地把头靠在椅背上,看着手机,她们似乎不会愿意被打扰,但也难说。她们的长相和衣着都不错,应该过得挺好的。健雅取出本子,想在纸上记一点东西。她做编辑前就有这个习惯,随手记下有趣的事。才三十二岁而已,老了吗?她想让自己平静点,这需要精致和准确的判断力。


“这是另一种生活方式。”
至少,健雅是这样认为的。堂妹也发现了这一点,说健雅现在对事物的评判开始高屋建瓴并且无懈可击了。这几年,保持同样的姿势已经成了她的标签或某种职责。可她刚刚写下“生日这天”几个字,就发现自己无法像往常那样流利下笔了。光线突然变暗了,窗外的阳光被一层厚厚的乌云遮住了。她放下笔,重新拿起书,任意翻开一页。这本书,她以前草草地浏览过一遍,还像有强迫症那样,每隔几页就在文字底下划上杠杠。重读此书,她发现自以为大有收获的地方,现在却显得晦涩难懂和模棱两可。
“……若能规定人不得将自己的心不能接受的东西放进脑子里,那么还有什么法律能比这更明智、更公正、更慈悲为怀的呢?”
书从健雅的手里滑了出去,她落入一个梦境。在这个梦里,她和爷爷都很年轻,在一条下雪的路面上,他们每走一步,身后都会留下黑色的脚印,很匀称但说不上美。雪花变成松软的、厚厚的地毯。爷爷问为什么。她很自信地说,那是李商隐的五言诗。爷爷笑而不语,不过,笑容和那些脚印融为一体,变得更长了。她明白,也许自己犯错误了,爷爷知道答案,只是想考考她。可是,当时健雅没把握住机会。
健雅醒了。
她清醒时的第一个念头是不好意思。那个会做点心的帅哥,此刻正站在她的面前。
“你睡着了。”这么说了之后,他笑了,“书都掉地上了。”
很短的梦。可现在梦的内容完全不见了,只有身体残留着做梦后的疲惫。健雅担心自己流了口水什么的,不过应该没有,她想去卫生间整理一番。
“不好意思。”她轻轻拿起了包,不想显得唐突和过于匆忙。
健雅洗完脸,收拾并调整好心态回来的时候,他已经走开了。
“你尝尝这个。”
咖啡是专门做的,一端过来就有强烈的味道窜入健雅的鼻孔。不同的是,他换了杯子,是绿色的穆斯林风格。她抬头看着他,像是让他解释一下为什么。
“嗯。”他捂着嘴,用力地清了一下嗓子。与其说是礼貌,更像一个直截了当但必须要做的交代。他问她,知不知道咖啡其实是阿拉伯人发明的。这是一个有点长并带有传说性质的故事,牧羊人发现他的羊群总是莫名其妙地兴奋,后来他找到了原因,是羊无意中吃了一株野生灌木的果实。
其实,他也不知道咖啡是什么植物的果实,不过这些不重要。
能够欣赏遗憾的人,才不会被生活的风浪击倒。
万事万物皆有所缺,我们必须尝试去原谅,才能在生活的细节中发现更多的趣味和机缘。


3.
应该说,城市属于那些偶尔或一直落魄
的人,市井和三教九流才保存着
城市的味道。
·风从山那边吹来·
一年前,杨光明觉得家里开始杂乱无章了,而这种情形一直在变坏,甚至发生了令人担心的状况。座机旁的小本子上记着所有事情,买菜、和某某一起吃饭或聊天,还有儿子杨小虎和孙子放学后要来吃她烧的鸡翅。若萱并不擅长做这些,但却乐此不疲。她把时间安排得准确又饱满,效率不高,但足够感人。
杨光明困惑的是,她为什么不写成一张张便笺,贴在相关地方。也许,她没有觉得自己陷入了某种困境,只是年龄大了,或是她父亲去世后,悲伤令她在短期内记忆力不能集中。她可能连这个都不承认,她只是不愿关心那些琐碎的事情,她是路盲也是脸盲。
但那又怎么样,即使出门坐错了方向,她也没把自己弄丢过。其实,也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。
有一天,杨光明打算出门的时候,若萱说她想出去走走。
“我可以的,我怎么能辜负这么好的天气?”
“嗯,不过你可要准备零钱,或者把想买的东西写在纸上?我还是和你一块出去吧。”
“你认为我不行?”
她换了衣服,打算买一些杨光明爱吃的水果。
刚进菜场,一只小花猫从她的眼前斜穿而过。她不讨厌猫,但不喜欢它凝视人的那个瞬间,让若萱克制不住地害怕。她走走停停,想起了杰克——她的狗,有它在自己就会有底气,就不会让野猫欺负了。可她不知道,那只猫只是碰巧路过而已。
后来,当若萱看到杨光明的时候,她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,她出门时拿了钱,可在门外换鞋的时候又随手放在鞋柜上。她的手机没有支付功能,她曾经说过,用手机支付像开车一样让人担心,不安全。后来,她又穿过街道,找到了一家生活超市,问人家可不可以先欠着,后来又说不用了。令人费解的是,她讲述买菜忘带钱的事,像是开玩笑,她知道要买什么,或者选择替代品,比如钱带得不够多的时候。
“我觉得有什么可操心的呢?”她说,“我知道,我的精神并没像志辉那样错乱,只是有点惊恐症罢了。”
志辉是她的堂弟,去年得癌症死了,生前有严重的焦虑症。
杨光明问她是不是在吃精神类的药。
“对呀,有些药是强制安定情绪的,但我不会像志辉那样胡来,你说呢?”她说的好像有道理,但有些轻浮。
“我知道我没问题,不过总有人说我记性不好。”


这是一个大问题,她意识到了,不要像她去世的母亲那样,渐渐地分不清谁是谁了。
“她总是这个样子。”杨光明对医生说,“有一天,她想洗了碗之后上楼看书,然后完全忘了。水在屋子里到处乱窜,后来流到走廊上,一部分顺着墙根流进了电梯。从那个时候起,我就不让她洗东西了,我们开始在其他地方过冬天和夏天。嗯,情况似乎有好转,可她觉得刻意的安排让她看起来像个笨蛋或弱者,但也接受了这一切。她不喜欢一年四季住在同一个地方,像生活在笼子里的某些动物。”
杨光明一直在留意她的变化。若萱不再记录,也不独自去买东西,不过她熟悉自己和儿子所在的小区,她和儿子聊得不多,但能聊到非常久远的事情,聊出生时的事,在什么医院和那天的气温,但无论怎样,都没涉及儿子父亲的事。儿子有时也会想,他母亲是不是把那段记忆删除了。
杨光明有次问她:“你知道《新闻联播》换了主持人吗?”
“你没看出来?亏你还天天看。”她说,“如果你真的分不清,下次体检你也查一下。不过,有个新来的主持人,我叫不出名字。”
杨光明笑了,他知道换了,不过他也不知道名字。可有件事若萱真记错了,她忘了杰克是哪年离开他们的。
杰克在她的手下生活了五年。
她从狗贩子那儿花钱买下它,用心地照料它,但养得并不好。
杨光明说不清是什么原因,他和若萱没有自己的孩子,这让他们烦恼但也没导致他们分开,也许他们应该生一个。结婚的时候,若萱三十五岁。
若萱对现在的结果有一丝不满和鄙视,不过儿子大了,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孙女。
若萱和杰克通常上午出去。杰克的长腿及柔软的毛发,和它温暖而不屈服的窄脸很相配,若萱从不担心它会丢。或许是以前受到的训斥和惩罚太多了,杰克忧郁的眼睛里藏着不少委屈,可依然忠诚和友善。
不仅仅是家务事,杨光明还独自打理着旅行社的生意,从南方回来后,若萱找了一个很老实的合伙人。其实赚了钱,但没人相信若萱能开旅行社。其他人觉得,是因为杨光明那段时间过于孤独,若萱想让他振奋起来。她对父母和其他朋友也过分关心了,她愿意独自承受某些事。
她相信爱。
如果生活之美总是藏在遗憾中
那么,我们不妨做人生的沉浸者。
享受平凡,接纳不完美。
.END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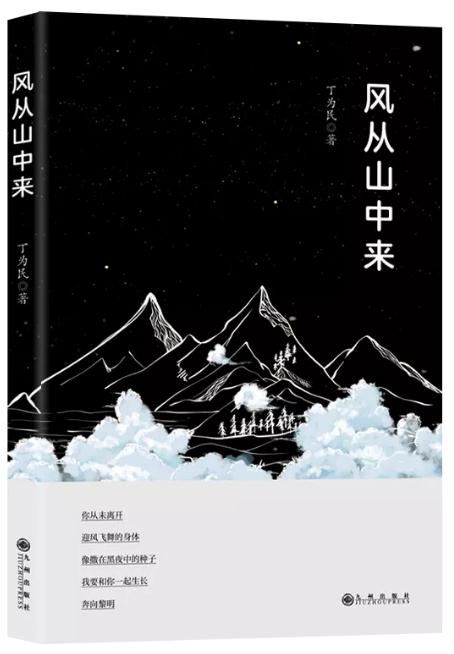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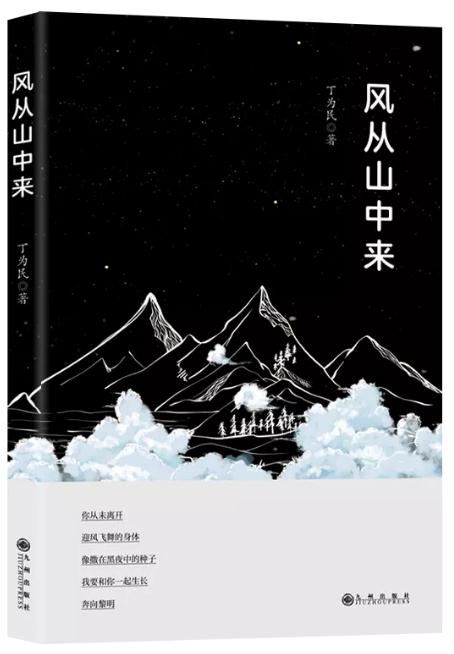
本书为短篇小说集,由九段独立故事组成,读者或可从中看到身边的某些真实的影子,以及作者对于人生的思考,生活的美好总是需要从苦痛中挖掘,而我们最擅长在挖掘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疗愈。
关于本书
丁为民,出身军人家庭,亦曾身为一名军人。目前定居深圳,多年来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尊重和喜爱。已出版作品《和岁月一起散步》。
>>中尚图动态